撰文/寧蓉(明靜)
攝影/王翠雲、簡淑絲、黃宗保
◎ 善良、堅強、樂觀的父親

在我的眼中,父親其實是一個非常善良、自律的人,不論什麽事總是先為別人著想。他曾說自己一輩子「沒什麽欲望,也從不亂花錢。」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幾年,補了又補都捨不得換件新的,每月除了理髮外幾乎沒有花銷,他的節約有時甚至被媽媽罵「吝嗇」。
但面對有人需要幫助時,他卻非常的大方。碰到無錢看病、買藥的窮苦人,他會將剛剛領到的薪水拿出來救人,而不管家裡還有三位嗷嗷待哺的小孩,氣得母親時常跟他吵架,罵他完全「不顧家」。
可是也有例外,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,被媽媽形容為「不顧家」的父親有一次到城裡去開會,開完會他到市場去吃了一碗當地小吃,酸辣羹;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,他馬上想到我們,想辦法帶了一大鍋回家。
當時的交通不發達,車子顛簸得厲害,回到家時東西已冷,且溢出了許多,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形容的那種美味。可是我吃酸辣羹時,特別感到那滋味此生難得,因爲那裡面有父親的愛。
在外人眼裡,我的父親是嚴肅古板的人,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有極爲善良細膩的一面。所以我童年時代,父親每次出差回來,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。
他對母親也非常的體貼,在記憶裡,只要沒有急救病人,父親總是每天清晨上班前就到市場去買菜,在家用方面也盡量不讓母親操心。幾十年來我們家大部分時間,都是由父親上菜場,一個學醫受過高等教育的男人,能夠這樣內外兼顧是很少見的。
父親還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,他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,正當青壯年時,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,時代背景下他和母親被下放農村,成了一名農夫長達十年(剛好是我念小學、中學時期)。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,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。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,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,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。
他常說:「吃得苦中苦,方為人上人。」
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,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,他常說:「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,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。」
由於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,使他成爲一個溫暖如火的人,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,這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。
◎ 父親的言傳身教

由於是醫師又當過農夫,父親從小教我們種地爲生的本事,常帶我和弟弟到田裡工作,並且認爲什麽事都應從最基層的觀點出發。我後來有興趣寫作,剛開始的時候,父親就常說:「寫作也像耕田一樣,只要你天天下田,就沒有不收成的。」
他也常叫我不要寫八股政治文章,他說:「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,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椰子一樣,不但種不好,而且常會從椰子樹上摔下來。」
他教我多寫一些於人有益的文章,少批評人,他說:「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,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;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,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,傷害生靈而不自知。」
有一回我面臨了事業上的瓶頸,回老家去休息,並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。當院長的他笑著說:「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,今年醫院收入很差,我正在想還要不要開那幾個賠錢的科別。妳看,我是開好呢?還是關掉減少損失好?」
我說:「醫院這幾個科別很重要,爲了治病救人當然還要繼續呀!」
他點點頭:「妳的事業做了這麽多年,爲什麽不繼續呢?年景不會永遠壞的。就像妳練習寫作,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,那麽,天下還有大作家、好作品嗎?」
母親常說父親是勞碌命,平日總閒不下來。他最熱心街坊鄰居們的健康,每當聽説有人生病了,總是很快趕去關心。
他是那種「有福不肯獨享、有難願意同當的人」。
他年輕時身強力壯,精力充沛,爲了病人常常犧牲寶貴的時間。有時正在吃飯或半夜休息時遇到急救病人,他和媽媽會馬上放下碗筷趕去救人。
他說:「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。」也因此我從七歲開始,媽媽就在我脖子上掛了一串鑰匙,每天放學回家自己煮飯燒水,幫忙照顧五歲的妹妹和兩歲的弟弟。
如今八十七歲的父親從未認爲自己老了,他的自律還在於他規律的作息。每天固定時間讀書學習、鍛鍊身體,國內外的大小新聞是他必看的。他常說「身體是本錢,沒有好的身體就沒有辦法幫助病人解除痛苦。」
但他在八十二歲那年做過一次脊椎手術後,身體因老化不像從前硬朗了,可他依然樂觀向上。這幾年來如果說我有什麽事放心不下,那就是操心年邁父母的健康。
後來我盡量減少出差,每天準時下班回家陪父母用晚餐,而這也是爸媽每天最大的期待與開心時刻,有時我也陪父親看他最愛的京劇。
看著慈祥的父親,想起年輕時嚴厲無比的爸爸,我眼中含淚感慨萬分:「要真正的讀懂他,可能需要我們用掉一生的時間。我們贏得了成長,而他卻輸給了時光。」
我又陸續送了上人的《藥師經講述》、《地藏經講述》、《靜思法髓妙蓮華》(序品、方便品)、《行願半世紀》等給父親,他歡喜得像個孩子,「好學不怠」地每天閲讀兩個小時。母親說:「他常常翻來覆去重複看。」
從《地藏經》的講述裡,他慢慢明白了因緣果報的道理,殺生的可怕,漸漸選擇棄葷茹素。一段時間後,他發覺自己的消化系統變好,原有的便秘狀況也完全改善了。從此堅持茹素並勸導家人、鄰里不要再殺生及素食的好處。
父母有三個孩子,我是老大。這裡面我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少,原因是我離家最早,工作最遠。我十八歲就離開家鄉到北京、天津求學,後來遠嫁台灣,工作更加忙碌,一年更難得回家一趟,有時頗爲自己不能孝養父母感到無限慚愧。
父親很知道我的想法,有一次他說:「你在外面只要向上,做個有益社會的人,就算是有孝了。」聽到這句話,我當下感動得淚流滿面,心想「一定要做個父親期許的好人,不讓爸爸媽媽失望。」
我後來開始學習寫作,在各地的鄉下小人物裡,常找到父親和母親的影子,他們是那樣平凡、堅強,又那樣的偉大。
◎ 報恩的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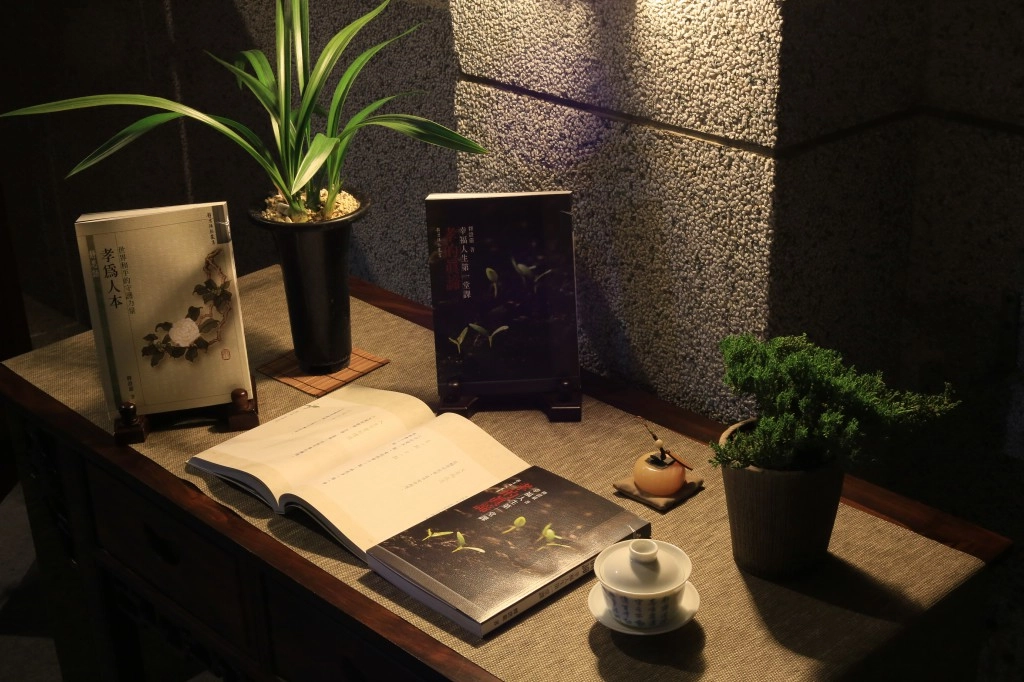
記得學校畢業剛開始工作時,平時不多言的父親找我談話,說:「做醫生,要做第一流的好醫生;想寫文章,要寫第一流的好文章;做人,就要做第一流的好人。」父親的話讓我銘刻於心並終身奉爲圭臬。
我常說我是最幸福的人,這種幸福是因爲我童年時代有好的雙親和家庭;青少年時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;進入中年,有了好的同修和好的善知識朋友。我對自己的成長總抱著感恩之心,當然這裡面最重要的基礎來自於我的父親和母親,他們給了我一個樂觀、良善、關懷、進取的人生觀。
但我能給他們的實在太少了,這也是我常深自懺悔的。每次讀到上人的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中佛陀的開示:
「假使有人,為於爹娘,手執利刀,剜其眼睛,獻於如來,經百千劫,猶不能報父母深恩;
假使有人,為於爹娘,亦以利刀,割其心肝,血流遍地,不辭痛苦,經百千劫,猶不能報父母深恩;
假使有人,為於爹娘,百千刀戟,一時刺身,於自身中,左右出入,經百千劫,猶不能報父母深恩;」
《長阿含經》亦云:「念護心意,孝敬為首。」至誠之「善」從「孝」開始。
讀到這裡,不禁心如刀割、涕泣如雨,這些年來我是多麽不孝。
我暗自期許「用父母給我的身體,做一個父親眼中的『好人』以報親恩!」

 Line客服
Line客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