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/吳瑞清(台北)
攝影/黃宗保、陳靜惠

攝影:黃宗保
初冬的天空灰濛濛的,除了偶爾奮力鑽出厚厚雲層的陽光,大部分的時候,總讓人的心沉甸甸的,不經意就跌回了塵封已久的往事。
*
「妳去看看黃媽媽家的『媳婦仔』,洗衣服是不可以開燈的,就應該知道我對妳有多好!」
記不得從什麼時候開始,對於養母平日的無理打駡,我早習以為常;但第一次聽到「媳婦仔」這名詞,心,硬是被刺了一下,差點忘了呼吸。
此時的我,才驚覺「養女」這詞,居然與鄰家那位一身破舊,每天似陀螺般轉個不停,且永遠看不清她臉部一絲表情的「媳婦仔」畫上等號。
「可是,我都叫您媽......」棉被往頭上一蓋,任由淚水恣意地宣洩,永無休止的夢魘及成串的問號,伴著我數不清的夜晚。
*
四○年代的農村裡,農業學校高等科畢業的父親,能賴以維生的僅是幾分薄田。父親為了增加一些些收入,偶爾會在滿天星斗的夜裡,到凜冽的山溝水壑間電魚,清晨再由母親挑到市集上賣。
母親未嫁時,是布莊、米店的顧店千金;婚後生活在大家庭裡,妯娌間輪流煮飯、洗衣......,每天等著她的農事一樣都不少。
一九五二年一月,母親懷了第三胎,逐漸隆起的肚子顯得格外地大。行走在前往菜園的路上,須經過一段不到一個腳板寬,大約五十階的陡峭石階。這條路,只能一口氣走完,中途無法駐足喘息;母親一天來來回回好多趟,有時肩上挑著水肥,但挺著大肚子,擋住了前路的視線,導致幾乎要側著走,儘管險象環生,生活還是得這樣過。
農忙期的田裡,男人忙著收割,家中婦人則負責煮飯及準備點心。此時,母親的肚子忽然疼了起來,立即產下一名女嬰;不一會兒,產婆大叫:「還有一個嬰兒!」果真,五分鐘後又一名男嬰相繼出生。一時間,「雙胞胎」像「頭條新聞」似的在村莊裡奔走相告,而我就是那個一出生,就當了姊姊的女孩。
嗷嗷待哺的兩張小黃口,對於當時的農村生活,可謂是雪上加霜。就在母親還在坐月子的一晚,昏黃的燈泡下,叔伯們與坐在桌角低著頭的父親,共同協議分家;原因只有一個,多一個孩子,多一張嘴要吃飯。
種菜、挑肥、賣菜......,即使母親辛苦地超時工作,但家中左支右絀的窘境卻沒停過,讓她佝僂的背影更駝了。由於父母親深信算命先生所說,母親與我相剋,因此才會三天一小病,五天一大病的輪流生病。
在山裡,頗具聲望的外公,是當地的「保正」,焗香茅油、樟腦油......家大業也大,也是母親唯一可求助的靠山;理所當然地,把我往外婆家送是唯一的路。
「這幾隻山猴子又來了!」阿來嬸作勢拿起竹掃帚追了出來,我們這群囝仔笑著一哄而散。
外公家鄰居圍籬的老欉含笑,樹下是大夥兒最愛「光顧」的地方,在含笑飄香的快樂時光,有表兄弟姊妹們作伴;含笑花熟悉的香氣猶存,歡樂的笑語更是只能在夢裡追尋!
當時二十五歲仍未出嫁的阿姨,是我的保母,而她最後決定終身不嫁,只要養我作伴。在長輩們的默契下,總覺得這麼決定,對大家都是最好的。戶籍登記辦好了,我的名字下多了一行字:收養關係──養女。
五歲那年,隨著做裁縫的阿姨養母北上,不出一個月,母親耐不住牽掛來探視;那時天真的我,以為是來帶我一起回家。依稀記得,那幾天,我像麻雀一樣,天天快樂地圍繞在她身旁。
到了母親要返家時,我身穿花布小洋裝,跟著大人們搭著二五路的公共汽車,揺搖晃晃地到了台北車站。
手上把玩著,母親剛買給我一顆顆圓滾滾、五顏六色裝著羊羹的小氣球,正在想像著橡皮筋解開時爆醬的樣子;一回神,發現母親已匆匆通過了剪票口。

我急忙摔掉汽球衝到柵欄邊,死命地爬了上去,望著母親漸遠的背影,聲嘶力竭地哭喊著:「媽!你等等我呀!我要跟您回去!」
此時,母親加快了腳步,只見站務員將剪票口的門「碰」一聲關上,快速的鉤上鎖,我哭得更大聲了。當時的我哪裡知道,任我再大聲,母親都聽不見,也不會回頭。
回程中,一臉鐵青、不發一語的養母,使勁地拉著一個哭花臉的小孩,回到那個原本就不屬於她的家。
許多童年夢想,隨著隆隆的車聲與汽笛的嗚嗚聲越行越遠;而縷縷的白煙,卻籠罩著年幼的我,久久揮之不去......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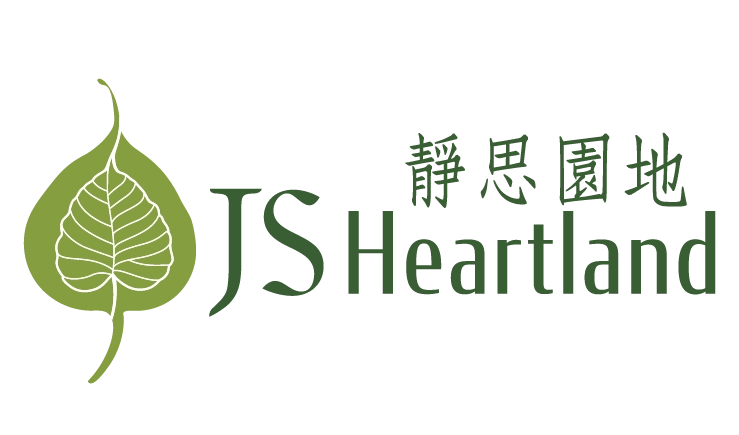
 Line客服
Line客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