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.蘇芳霈
行不繫於所欲
那年初遇慈師父,精舍陶藝坊方興,乘國際慈濟人醫年會回精舍,與同行醫療人員欲探究竟,三三兩兩漫步過菜園那一隅。
小徑初醒似地一路綠漾,陶藝坊走道外盆盆花樹婆娑。
那些種花的陶盆,大多是慈師父嘗試做陶時,同一件作品製作過程中,由於新舊陶土軟、硬、溼、乾程度不同,素燒時,火熱熨燙過層層迥異陶質,水氣奔騰而出,陶作開始皺縮,在那個過程中產生了剝裂。陶作失敗,慈師父惜物,就把這些有瑕疵的素坏陶盆拿來種花。
一盆陶一盆花堆出來的屋外景色,有著慈師父純樸節儉善用的美德。舊時美好藝術生活的美,有如真實過後的回憶。
遠遠見慈師父步履蹣跚迎來,「我們在那兒見過面,那麼熟悉?」慈師父問我。我也有同感,只是愣愣地,傻傻微笑不語。
同行師姊便向慈師父介紹︰「她是藥師,也很會做陶、繪圖,還寫文章出版書籍。她的藥局星期六下午有陶藝治療,我有一次好奇,也去湊熱鬧捏了一個作品!」慈師父眼睛一亮,趕緊招呼我們進陶藝坊。
著作:蘇芳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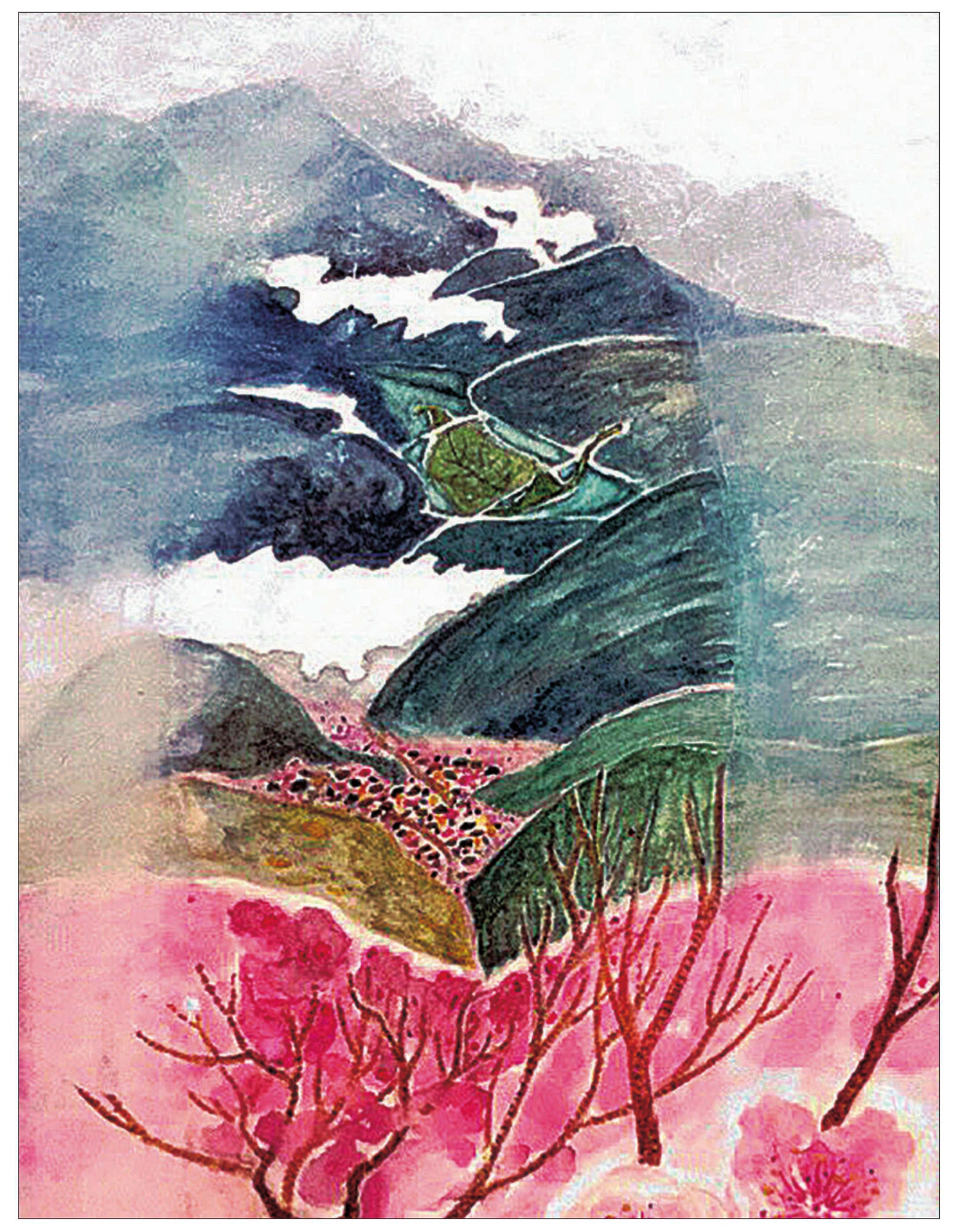
慈師父先是從架上取了一個素坏陶碗給我,讓我用毛筆沾釉色畫圖在陶碗表面。
陶作表面的圖樣顏色,分兩種情況而為。一種是尚未燒成素坏前,先在微軟的陶作表面,以雕刻針刻畫出喜歡的紋路或圖樣,再素燒;素燒後,再以噴槍放入想要上的釉色來噴,藉由釉色噴量深淺不同,在釉燒時會產生色澤變化來豐富陶作。
另一種是陶作完成皆素燒好了之後,再用毛筆沾釉色在陶作表面作畫。這種方式比較不穩定,因為釉色上得不夠厚時,釉燒不呈色,或說色澤極淡,圖樣便容易因釉色呈現不一而失真。
以往我習慣於前者。但慈師父要我在素燒好的陶作上畫,我就畫了一個簡單的貓睡圖,畫的過程比平日慢好幾倍,因為要斟酌釉色的厚度是足夠呈現美麗色澤緣故。他看了後說:「好口愛!我也喜歡貓咧……」我們被他平易近人的慈祥和質樸的臺灣國語,逗得笑呵呵……
舊時陶藝坊尚無展示間,只有用鋁門窗建成,靠牆簡陋的釘了木桌板,牆上有好多插頭,屋內也擺了舊長方桌,一桌堆著花器、另一桌堆滿陶碗、小茶杯,再另一桌中間以高木架隔開成兩個工作桌,木架上也放滿陶碗;而宇宙大覺者座臺就在靠近裏邊燒陶的另一個長桌上,對面的牆堆滿了裝陶的容器,很是克難。
時光凌空一劃,幽幽靜靜。
光線自窗外亮進記憶,慈師父侃侃聊:「我自己傻傻什麼都不懂啦,師父要我畫佛像給他看,我就傻傻地畫給師父看。畫了好幾次師父都不滿意,到不知第幾次師父終於說可以了!我好高興!就依照那個像胡亂做,變出宇宙大覺者!師父眼力真好,他說好就是真的好。你們看,做起來這麼莊嚴!到現在我都懷疑這是我的作品!」
慈師父雙手珍貴地抱著粗製品,一直笑得合不攏嘴!
從緊張忐忑到做得熟稔,歷經多少歲月。我彷彿看見河中有倒影,不再漂縷著被打散碎苦的月色,而是一條長綿如漣的祈禱回聲。
他老人家一邊講,一邊自嘲著笑。他的笑容、音語,總是發於真摯,行不繫於所欲。

即使早年環境克難、人手少,慈師父仍專注投入,樂在其中。
味不絕於什調
他很疼孩子,就是慈母的味道。
我去陶藝坊探他,他總是從牆架上取下一盤一盤的零食,要我品嘗。有糖果、有話梅、有餅乾。
「咱慈濟草創時,有夠辛苦,沒地方住,有草蓆有木板就很好了,腳都還無法伸直。三餐不繼,還欠債。」那是一個瑣碎年代,要開啟另一種完整的可能。「欠債好多,我們什麼都做,織毛線衣、農作、糊水泥袋、做嬰兒鞋……但都賺很少。有一次種稻,打算可以還錢,沒想到經驗不足,稻都枯黃顛倒了……」他凝眉斂色講過往經歷,傳承續脈這本用韌力寫來的生命筆記本,滔滔不絕。「要惜福喔……」說著說著,就把盤裏剩餘的零食往我手上堆……
靜思精舍常有外客來訪、海內外師兄姊回來向上人報告、營隊回精舍,或師父們出坡被小蟲子叮咬、受傷等等,都需要設醫療站守護大家的健康。輪值精舍醫療站時,每每要趕火車了,就看他老人家拿著我們的便當衝入廚房,問其他師父菜炒好了沒?「卡緊!卡緊!孩子會趕不及上火車……」還會一直招手要我們去挑要什麼菜色。廚房內熱氣蒸騰、煙霧彌漫,師父們揮汗炒菜,一大盤一大盤都是師父們出坡親手栽種出來的青菜,一盤盤的愛,心靈滿是悸動。「多拿一點,得要吃飽飽喔……」
慈師父拿來一只紙袋,把我們裝好的便當一一放進袋子,又再去拿水果放進去……一顆慈母心,一直以不同面目與溫度,活滋我們靈魂。
這一幕,有如一扇音隙裏傳來的爐火,一次次蹣跚而殷切的背影裏,有著彼此矜離無言的腳步聲!味不絕於什調!

位於精舍一角的「陶慈坊」是營隊或是訪客必定造訪的定點(攝影:左/黃炳添,右/陳正忠)
心如詩的意志
新店靜思堂啟幕,《慈師父講古》一書出版,正值尼泊爾震災義診隔年,靜思堂有一個空間布展慈師父書中的舊時物。我坐在一旁靜靜聽他向其他人侃侃說道:「以前白天忙碌晚上讀書,師父說我們要有知識,教我們讀《論語》。師父很嚴,我常常聽不懂,有時累到睡著了,眼睛還睜著不敢閉……」大家被他逗得笑歪了腰……
出生在日治時代又遭逢戰爭,學業斷斷續續,「不識字也要寫字啊……」慈師父說:「你們看,作畫結束不是要寫字,陶作上也要寫字。剛開始學人家依樣畫葫蘆,可是畫不成葫蘆,倒像草啦……」一夥人又是一陣催淚的笑開來。「但是你們看,我現在可以這樣寫了,雖然不是很美,但看得出是什麼字。師父常說要『多用心』,專業要有雄心,不要有野心。不是專業,做久了,也就變成專業。我們就是做中學,學中覺。」此時笑聲化成了讚歎!
慈師父墨畫有著樸拙之美。他畫慈濟草創時種種:畫上人抱著甘蔗葉走在借來的牛隻前,引誘牛隻往前帶動,後面的他雙手抓住鐵耙用力犁田的情境;畫精舍在一片美秀山田間;畫他所見慈濟一路走來既甘美也萬苦千辛的一切……心如詩的意志。

慈師父透過水墨畫,畫出記憶中的歷史。
而今陶藝坊的入口處,他用毛筆墨汁親筆寫下「陶慈坊」三個字。字如人,那般慈悲、謙和、樸實又充滿愛。
法脈宗門精神的無量心燈,是他手作的聚寶盆。
盆燈表面除了陶鑄著精舍圖樣,並有慈師父的墨寶;即《無量義經》的精髓──「靜寂清澄,志玄虛漠,守之不動,億百千劫」。於是乎精舍的長廊一到夜晩,黃澄澄溫柔的一盞盞無量心燈,便來點亮人人前行路。
對慈師父而言,手拉坏、作畫、精舍草創前艱辛賺錢來堅持做善事的每一樣工作,無不都是一種修行。
他充滿藝術天分的靈魂,在陶藝世界有如夜裏那串微醒餘香的玉蘭花、早晨灶鍋上冒煙的白米粥、精舍後山蒸騰的純白山嵐……
他的為人充滿溫度。身上舊衫褲、早課時因膝關節退化艱難久跪的身形……母親再也無法走太遠的路去賞花了。
慈師父也像墨色凝固在絹帛或紙面上的一塊深黑,經過水的滲透,溼潤毛筆的筆鋒一次又一次地暈染、渲刷、沖淡,墨色與紙絹的纖維開始了交融,發生瀅潤如光層次的色澤變化。他融入智慧的總總,溫潤如玉,是一片遁入湖水還柔軟的葉子,有顏色回味的痕跡。心如詩的意志,浮葉要另帖了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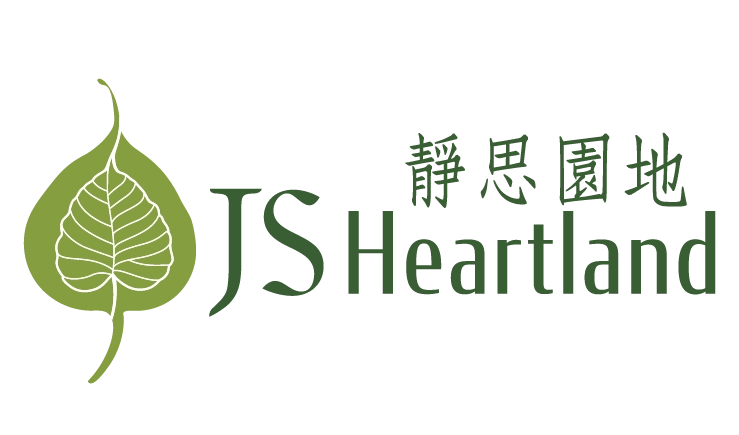
 Line客服
Line客服